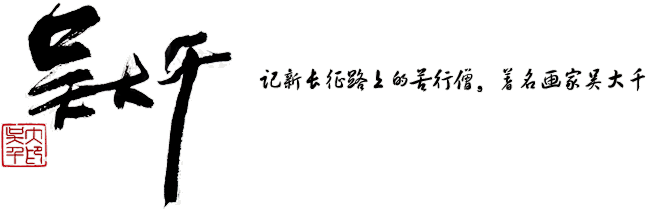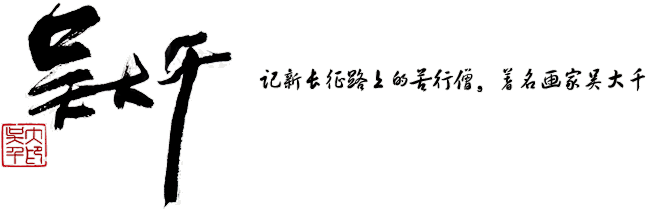
半疯堂主的胸中丘壑 一一素描画家、行者吴大千
发布时间:2018/06/21 阅读:4015次
半疯堂主的胸中丘壑
一一素描画家、行者吴大千
愚石
初见吴大千,以为此兄是民国人,且还是那种置有田产数十亩,纳智慧,性达观的乡贤。移步面前的人身着藏青色粗布长衫,那是一件皱巴巴的、复古风格的长衫。十一年前着长衫的人突兀地立在你面前,你要么觉得另类,要么会对这种人产生疑虑,或者只是被什么扎眼的东西晃悠的心生敬畏。一件复古长衫,现代人穿在身上,产生的效果极有可能不协调,亦极有可能被人误以为是曲艺界的人物,或是像我们平常所见,有的人干脆穿出不伦不类的效果来了。然而,那件不新、不破、不旧的长衫罩在此兄身上竟是格外贴切。面带笑意的他身材中等偏瘦,硬实、健朗;长发、美髯、面庞清濯,唯双目炯炯,透着老辣,让人觉察到他亲和力后面缊有一股韧劲。我的第一个念头,此人看似有装模作样的实际,却委实不是什么泛泛之辈。从他谦恭的举止,不徐不缓的谈吐中,我揣测,如果无甚意外,眼前的这个样貌奇诡的汉子,是个有故事,或出过事故的家伙。迎着他的目光,我看见了他的眼眸中的坦然、以及不羁的光彩,那光彩忽明忽暗,蛰伏着一些不知所以然,实际上,那看似不知所以然之中,藏有不易察觉的智识和见解。伸手去握他的手,结实有力,粗糙的手掌令人又是一惊,心下怀疑这是一双拿画笔的手?未出声之前,他的眼角往上挑,胡须有规律的抖动起来,甫一开口,西北口音里揉搓了些许软侬细语,到让我不好揣测他是何方神圣?众人围上前,寒暄,年兄逐一介绍各路大仙,有书法家,民营企业家,作家、诗人,体制内的这长那长;指着民国范的这人,年兄到是留了一手,只轻描淡写地介绍说长胡须、着长衫的人是个著名画家,浙江美院毕业的画坛怪才。其实,在坐的十余位,只有我和另一王姓年兄是第一次慕名见到他。
一般来说酒桌上的唱酬总是乏味的时间多,各说各话,各有各的情绪宣泄,或应景目标。当时,众人对这个民国范的,名大千的家伙都敬意满满。我是年兄叫去做陪的,原本就把自己放在陪他酩,陪他笑,陪他瞎胡闹的位置上,自然好话多、歹说少。酒席上,气场完全在他那边,但他的眼神里及话语中透有些许江湖气,还有隐逸于山野之中的智者的狡黠。他做得蛮像是客居于此地、家境殷实、又无拘无束的员外。场面上,他亦不讲客套,虽说没有拉开喧宾夺主的架式,但少有拘泥。酒桌上的他不温不火,得体自在,既不骄情,又没有生分的套话。偶尔表述一下自己的观点、对插科打诨即时回应,笑起来也不含糊,其间,还每每主动站起来,双手端杯向在座的例位一一敬酒。而后,先干为敬。酒过数巡,众人都熟络起来,交流起来愈发直接,话语里的俗世味道也愈来愈浓。既便如此,我还是感觉到他身上具备某种特质,这特质是什么呢?是洒脱,是狂放不羁,还是入世的觉悟?
酒过数巡之后,他的胡须上便沾上了酒花,不经意地他会用手指挦一把,然后很有味地放到嘴里边舔一舔。微醺状态下的他,笑容格外灿烂。也只在此时,我才见识到他的憨态与坦诚,那神彩飞扬处,呈几分豪迈、干练和野性。与南方的人豪气相比,他的豪爽劲内里、似有黄土地或者高原人的耿直仁厚。那天宴聚是场大酒,众人呼三吆四,喝得尽兴而痛快,气氛热烈异常。大伙儿因他的爽快少了拘谨,我亦不曾有初识或陌路人的尴尬。从喝酒的速度上就能够看出,围绕他展开的话题或恭维,都是以举杯、干杯结束的。几瓶白酒、红酒很快见了底。席间,年兄趁着酒酣耳热交待散了席,让我一块去他家陪画家喝茶。当年,我和年兄老徐都还是贪杯、豪迈的可以的主,只要吃席、喝酒、唱酬应景,既然喝上了,不撂倒个把人那是绝对不会罢休的。他一交待清楚,我亦未曾多想便痛快地应允了下来,其实心里亦有结识结识吴姓名大干这家伙的意愿。当年,我对这个敢用大千做名字的家伙除好奇外,还是有不少疑问的。此人相貌、装束、谈吐,还有浑身散发出来的略带狂野的东西,是个人魅力吗?还是欲盖弥彰、装傻充愣?或者,原本就是个有趣的人物也未可知?
酒后的闲话,一开始可以说是漫无边际的,应当是酒精的作用,坐在年兄家的四个人,有三位亦然进入到了亢奋状态。信口开河抑或不着边际、不靠谱,对于善饮者而言是一种境界,是大话开篇、思绪与表述之水库打开闸门无所顾忌倾泄的借口,也是饮者相互间逐渐靠近对方三观的捷径。它有一个被善饮者(贪杯之人)奉为至诚待人的最不要脸的托词,所谓酒逢知己干杯酒少,(醉话连篇有人接也。)太白说,唯有饮者留其名,可是对真正的唯生存为目的者,以及争物质利益为先、或在生活中有心理洁癖的人们看来,贪杯的人是人格有缺陷的,至少是惹人嫌的。
大干这家伙倒是洒脱的很,到年兄家后,三下五除二便把长袍脱下,往上拉了拉灯笼裤裤管,一屁股坐在了地板上,全然不知什么是拘谨和客套。年兄泡好茶,放上茶点,话闸子一打开,哥几个竟是十分投缘。天南地北,天文时空,时势人物,历史文哲,一通瞎侃,让画家吴大千江湖性情即刻暴露了出来。他大声吩咐年兄老徐:徐兄,快快上酒!似乎无酒便辜负了有趣的话题。于是乎,除另一年兄老王喝一盏老茶助兴,我们三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茶酒夜宴。
那一晚说不上喝的昏天地暗,到也让三个夜饮者直接奔向了醉意至深之处。
十年前的那次相聚我至今仍记忆犹新,也就是从那天开始,对于吴大干其人,我有了初步认识,并且有了想要不断了解、关注他的念头。那天的吴大千,让我乍见时好奇、接触时惊奇、而听了他的经历之后,更是很有些个惊为天人的意思了。
十年前的吴大干四十出头,但他早已是个名扬天下的新闻人物。何以见得呢?他何德何能,以至于只要搜索新闻,便可让人对他肃然起敬?
26岁那年,在绘画艺术上寻求突破的吴大千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,他要像徐霞客那样游历干山万水。徐霞客是他儿时的偶像。
山洼洼里的放羊娃,圪梁梁与辽远的天空很近。他走出那片土地时,应该身后还有青海花儿的旋律悠长,深情的词语紧拴游子之心的情景和声音。他在浙江(现中国美院)美院完成了人生的第一次升华,回到家乡青海西宁后,日子刚平稳下来,他突然做出了完成儿时梦想的决定。那一年,成了他人生快车道上的急转弯,要么进入追求艺术成就的快车道,要么一无所有。但他的心性是奔放的,胸襟足够宽广,装得下世间的山川,每一座耸立的山,每一条沸腾的河流,既便是耸入云端的雪域高原、莽莽昆仑,乃至于黄河、长江他都想揽入怀中。
八千里路云和月。吴大干选择的路,岂止万里?也许比路途更为艰辛的,是心路历程的挫折,是人情世故之于现实的压迫和孤立无援时的前途迷茫。他的长征是悲壮的,个人的,充满了古希腊神话悲剧英雄的色彩。他不是西西弗斯,不是普罗米修斯,他只是孤独的旅人,餐风露宿,艰难跋涉,以脚踏车做马,以前路的景致为界碑。他走的很坚定,很执著,时而踉踉跄跄,时而了疾风剑豪,时而欣喜若狂,时而仰天长叹……他在追梦,他在做苦行僧,他在放飞心中的鹰或理想。
他披荊崭棘、披星戴月,疯狂地、流浪汉般的走了十一年,从青年走到成熟的青年。
他把祖国的山山水水,风土人情印在了心里。他胸中装丘壑、画风陡然有了气势和韵味。因而,在他后来的每一幅山水画中,都能见证纵横奇峭之魂,那些都来自于亲历,来自于仰视后、深情的注视后,与之默契的交流的心得。他读懂了空谷足音,感受到了层层深厚,磅礴气势之于山川与自己灵魂的融合。他在自然中找到了自我意识的再升华,完成了画风的钢的淬火及其艺术定位。214座名山峻岭,47条江河、湖泊,2824个城市乡镇,无数条宽阔的,狭窄的,坎坷的路,以及数不清多少次陷入到险恶之境。他一路风尘十一载,讨饭将近四年,被人们当做疯子、流浪汉、怪物。他的所见所闻,内心的感触,所到之处与人相遇,交流的经历,是一般人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得到的。
在路上的吴大干,意气风发的吴大干,神秘而执拗的吴大千,一个人面对险恶之境几乎只能靠神明佑护的吴大千。他是探险者,骑行者,艺术的殉道者。
出门时,他身边带着的是母亲为他准备的家乡思念,一包厚重的观音土,一包浓重的思念,这包圪梁梁上的土圪塔,既能解对家乡的思念之苦,又能治水土不服。其实,在路上的十一年,吴大千所经历的孤独、困境、艰险以及对精神世界的不断探寻,对其本人而言是一笔无法用数字计算的巨大财富。(十一年单骑走中国的第七个年头,吴大千曾回到家乡西宁,在短暂的休整期间,依照家乡的风俗,他为父母画好了棺椁后,重新踏上漫漫长路。)
第一次见吴大干的那个晚上,谈及八十年代末,九十年代初的那些堪称英雄的探险者们,他如数家珍。长江漂流,黄河漂流,独闯戈壁滩罗布泊,人们从好奇、惊诧、不理解到钦慕……那是个成就英雄的年代,是一代青年渴望充分展现自我、实现自我价值最好的历史时期……是处于精神青春期的人们挣扎成塑像的时间段……尧茂书,长江漂流第一人;雷建生,郎保洛们,用生命拥抱黄河……九零年代的余纯顺,戈壁滩上升华的不屈不挠的灵魂……这些人,在吴大千心目中,亦然是英雄的标榜。因此,后来用十年时间走遍中国大好河山的他,用绘壮丽河山,写民俗风情的方式成就了自身的梦想及个体生命的价值。
醉了的吴大千看上去更像个单纯的少年,无论是奔放的性情,还是个人趣味,有幸见识到他醉意至浓的面目,你除了认为他既疯且十分有趣外,至少不会很快忘记你曾与这么个家伙有过交往。
第一次醉意朦眬的坦然、坦诚、坦率,给我的印像是,这个有趣的家伙。见过几次面后,我常常在心里嘀咕,也许这家伙内心乃至灵魂一定会是更有趣的,或者至少有有趣的东西深藏于彼心中。那晚,谈及余纯顺独闯戈壁滩,他的描述是生动的,让人仿佛亲眼目睹那个孤胆英雄,孤单而执拗地走在浩瀚无垠的大漠之中,看不见孤烟、绿洲、甚至翻卷的乌云。他在寻觅自己埋在沙漠某一地点的补给和水,他每一步都走的很艰涩、艰难;最后,吴大千卧在地板上,用一个卧伏的姿式,形像地展示了探险家余纯顺成为永恒姿态的身形。那晚,他讲了学生时代对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认识一一他说,我们用一根绳子拖一个小瓶子在地上……他就那样表达学生时代对社会最直观的爱恨情仇……这种表达方式让我们当晚每个人至少多喝了二两烧酒,而我也从另一个方面,知道了大千世界里有许许多多种行为的表达方式,也有许许多多的人像我一样,对世事的认识来自于亲历的苦痛后的再认识,虽然它不一定完全一致,(也有可能南辕北辙),但至少有些许的共鸣之处。
吴大千多才多艺,他对陶艺、瓷艺、杂件收藏、宗教信仰、乃至民族歌曲、民俗文化都颇有心得和造诣;他的书法也颇有韵致,飘然轻巧中见功底。他唱青海花儿,即似断续倾诉中深藏致诚,又有苍凉、沉郁的深情表达,令人心神荡漾;他高歌蒙古长调,悠远绵长,仿佛旷野神韵与流云一同飘逸,声音里饱含人世的忧伤,憧憬,对爱情的期许,以及北方以北的豁达、乃至孑然伫立于高原之上的悲壮。每一次听到他粗糙的嗓子里发出的音质,我都会涌上莫名的感触,因为那里面有人生、有故事、有对生命的理解,对生活磨练的达观,和某种意义上的不屈不挠。你说它是圆融也好,是妥协也罢,但我以为那是真实的阐述,是心灵的释然表达,是对个体生命的再认识。而且,恰恰因为我自己很容易陷入排山倒海的忧伤情绪之中、去感怀人生和世事,所以与吴大千在一起对酒当歌,极易陷入醉意后的情绪亢奋之中,还有对生命意义的悲悯意识……
与吴大干交往的这些年,我一方面有对他个人性情的认识。他是个我有一壶酒,足以慰风尘的情怀浪子,是一个在漂泊中找寻生命意义执着理念的人。另一方面,也让我更深切地意识到,其实漂泊还有另一层意义,既慰藉心灵的空白,寻找人生中永不厌倦的地域,它应该足以化解红尘凄短之于生命的遗憾。吴大千的漂泊,应该与他对艺术的执念相关联。
新安江,一条河流,一条美且温情脉脉的河流。它发源于黄山山脉与白际山脉之间。明末清初之际,它既是徽商的母亲河,又适时地蕴育了"新安画派‘’文人画画风的形成。这条河以中国独特的徽文化与自然风光、古村落美仑美奂的结合而著称于世。
一直在路上的吴大千,一面贪婪地饱览壮美的大好河山,一面找寻能让自己的脚步停下来、能使自己满怀疲惫的身心驻留的地方。在黄山脚下,在新安江的发源地,学生时代就对"新安画派‘’心怀崇敬的他,选择另一种开始,在此安营扎寨,洗尘、留连、整理作品,亦或许只为此处的风景,只为游历至此感受到的心醉神迷。总之,他停留在了黄山脚下的宏村。
历史上,黄山、新安江畔,是文人荟聚之地,而新安江、及江之畔的景色本身就是一桢精致的山水画。
在中国画画史上,新安江,新安画派亦无疑有着独特的地位。
自明末清初之际,新安画家逐渐形成崇尚"米倪‘’之风的画派,其画风讲究枯笔皴擦,简淡深厚。发展至成熟期,新安画派以其务实,繁简、疏密统一,用笔如作篆籀,洗练凝重,遒劲有力,以及在行笔谨严处,有纵横奇峭之趣,所谓"黑、密、厚重"自成一格的画风体系。传统意义上,新安画派除却传承,并时有发展和变化,亦使得它在艺术领域独树一帜。发展到近现代,其代表人物既是当代画家黄宾虹。
黄宾虹是徽州歙县潭渡村人,有白宾虹,黑宾虹之誉,其所画山川,层层深厚,气势磅礴,惊世骇俗;其干墨淡笔,皴擦点燃之用笔,自成一体,不拘世俗。
吴大千在黄山脚下驻留,与其说是一种选择,不如说是他听从了内心的召唤。在此期间,他创作了大量的山水画,也使自己的画风有了根基及发展创新的艺术积淀。他师法于大师黄宾虹,在艺术实践中亦有自己的再认识,也可以说,他十余年游历所画的写生画,无形中成了一座宝库。师法大师加之师法于自然,使其作品不但栩栩如生,不同凡响,而且有最直观的根基,甚至灵动的魂。
丘壑在心中,山水画自然有灵魂。
吴大千曾自诩为"半疯堂主",后改书斋为"半风堂",我以为"半疯"比之"半风"有趣的多。这些年,他还是一样的热忱、洒脱,执着。艺术创作上,他更加严谨。我认识吴大千时,他己名声远播,干山老人,青年旅行家,新长征路上的苦行僧,当代著名画家,这些名头,都不如我以为的,从辩识艺术家的气质来的更直接。半疯,是谓对人生追求的执念和契而不舍,是谓对生活的认识和生命状态的理解。这个出生于青湖古城西宁的放羊娃,内在的艺术气质,憨厚的人品,爽直且狂放不羁的性情,到是更让我倾慕了。
一幅长卷《锦秀中华》,它的意义不单单是水墨重彩下的大好河山,它可能更具一种象征意义。一个人,走遍中国的二千八百多个城市,攀登或阅览214座名山大川,47条江河湖泊,除了文字记录,还用写生的方式描画下来,其间一定有遭遇过的疾风苦雨,有煎熬之际的无人响应,艰难的攀爬,跌倒后的痛楚,不知前路在何方的惆怅……一个人,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,藏北无人区,其间一定有烈焰的烘烤,孤寂的挣扎,甚至面对死神召唤而无所畏惧的悲鸣……
十余年来,几乎每年都要与吴大千在某地相聚,每次相聚都一如君子相交,不是淡如水的那种,(吾愚顽,离此境界甚远。)但我与吴大干的聚首,的确是酒浓时分坦荡赤诚相待的雅聚。此一意境,以缘聚谓之恰如其分。从吴大千的话语和近期的画作之中,我发现了他的改变,也愈发对其于生活磨难中,关于艰难世事的感激之意有深层的感悟及钦佩。初心仍在,追求依然不可懈怠。画画,云游,教书,对酒当歌,出世与入世,参禅修身,吴大千对艺术与生命本真的理解,会令其达到一个高度。这个高度,也许是绘画艺术的象牙塔,亦或许是历经沧桑后成就的人生价值的完美体现。他活出了个人生命的本质,他活得异常精彩,他仍在完善、修正生命价值观、世界观的路上疾步行走……
2018.初春
於愚石斋